【上床何忌骨肉亲:母子互动札记】(6)(24/27)
着]。
我也就不作怪了,身心上获得了极大的刺激与快感。到了我家的木薯地,下车后,母亲训了我一句,[坐个车都不会]。
然后开始了劳作。
往 茂盛得遮天蔽
茂盛得遮天蔽 的木薯叶已经干枯萎缩掉落,只剩枝干 ,也恢复了黄土地的面貌。
的木薯叶已经干枯萎缩掉落,只剩枝干 ,也恢复了黄土地的面貌。
被吸收了养分的旱地土质疏松,但也得小心翼翼,力求完整地拔出木薯,要力气也要巧劲,不知道为什么,无论我实践了多少次,做得总是不如母亲完美 。
剥脱后装袋,一包包地扛出路 ,附近的猪倌适时做起外快,用三
,附近的猪倌适时做起外快,用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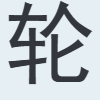 车帮你运回家中 。
车帮你运回家中 。
也有收购商驻点,现场收购结算。
也有 选择运回家中 ,作进一步处理,脱皮,晒干再出售。
选择运回家中 ,作进一步处理,脱皮,晒干再出售。
对比起来,后者获得的经济收益比前者大,但功夫多了不少。
与北方机械化规模化作业不同,我们这里务农似乎陷入一种奇怪的矛盾。
我们明知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但还是选择了面对黄土背朝天,农耕文明的基因深入骨髓。
一方面,农作物的最终收获,成为了我们饮食的主要辅助材料来源,比如,木薯生粉 ,在传统油坊炸出的花生油。
直至今天,这两大件仍是农村出外谋生的 钟
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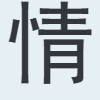 携带之物。
携带之物。
一小块一小块,表面经晒后泛黄、内里雪白的豆粉 ,依旧替故土滋养着奔向远方的游子。
另一方面,充裕的农作物是家里的压舱石。
如果仅仅是食用,根本不需要耕种这么多。
收入微薄的广大农村,一旦有需要,只能把多余的粮食换作金钱。
小时候,都经历过卖稻谷换学费,孩子不懂事,看着收购商将谷仓的谷物装袋运走,知道能换来令 渴望的钱币,只觉欢喜,哪知道大
渴望的钱币,只觉欢喜,哪知道大 背后的苦涩,以及
背后的苦涩,以及 民币浸透的血汗。
民币浸透的血汗。
在父亲经济沉沦的那几年,我听
 说过,母亲一
说过,母亲一 千辛万苦
千辛万苦 持的木薯,瞬间成了修补滴水天花板的资费。
持的木薯,瞬间成了修补滴水天花板的资费。
后来我回家看着白色天花板上一道深灰色的修补用料,只觉是一道划在我们 生中的伤
生中的伤 。母亲几乎没有提及这件事,可我分明能想象到她当时的绝望与悲苦。
。母亲几乎没有提及这件事,可我分明能想象到她当时的绝望与悲苦。
一个小意外事件,能重创一个家庭。
就靠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把孩子拉扯大,乃至供书教学 ,大 们用这一句话教育了孩子一生,成为不少农家子弟
们用这一句话教育了孩子一生,成为不少农家子弟 后厚重的回忆,也鞭策着他们快快懂事,挑过养家的担子。
后厚重的回忆,也鞭策着他们快快懂事,挑过养家的担子。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